一个纳西族人类学者的学术心史 ——访云南社科院杨福泉研究员
此文原载《民族论坛》2013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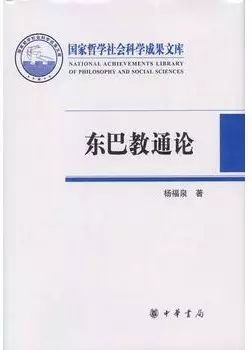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你今年出版的专著《东巴教通论》应该说是目前研究东巴教最权威著作了吧?
杨福泉(以下简称杨):我确实花了很多年的功夫来写《东巴教通论》,可以说是迄今比较系统地论述东巴教的一本书吧。它在200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2009年结项时获得了优秀等级。2012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3年被评为云南省第17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徐:这是你的最高成就,或者是代表作?
杨:从研究东巴教方面来说,应该说是我的重要代表作。此外还有一本专题研究东巴教一个神祇和纳西传统生死观的《生命神与生命观》,这是一本聚焦在东巴教生命神“素”的微观研究专著,辨析过去常常被翻译成家神“素”这个神祇,这本专著的主要观点写进了一篇论文《生命神“素”及其祭仪》(The Ssu Life Gods and their Cults),选入了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奥皮茨(Michael Oppitz)和瑞士人类学家伊丽莎白·许小丽(Elisabeth Hsu)主编的国际纳西学名著《纳西摩梭民族志》(Naxi andd Moso Ethnography)一书中。另外我有一本下功夫比较大的民族史研究的专著,书名是《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这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本书在2009年人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2011年人选了“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此书获云南省第10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徐:《东巴教通论》何时出版呢?
杨:这是中华书局今年才出的。2011年全国人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有两本宗教学的。一本是中国社科院宗教所邱永辉教授的《印度教概论》。还有就是这一本。
徐:它印数也标上去了,1500册。
杨:全书68万字。中华书局还允许我插图插了200张左右,其中有很多是在田野调查中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其中有很多也是老照片了。虽然它出版社处理为黑自的,但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图和文字可以有个对应,不少图都是珍贵的资料,很多人事和场景都变迁了,这些图片成了历史的定格。我现在回顾一下,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做学问进行田野调查以来,照相机一直不离身,现在看来这真是太重要了。
徐:人类学重要的工具就是照相机。
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到现在,我去过的很多乡镇里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包括东巴和普通百姓,有很多场景也已经变化了。包括丽江古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场面,我都已经拍了照,不仅用笔,还用图像记录了变迁,比较庆幸。
徐:现在倒回去讲,我们先讲讲《东巴教通论》这本书,讲讲这本书的观点和创新的价值。
杨:东巴教的研究,以前国内的很多研究仅仅局限于纳西族,因为东巴教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或纳西族的原生性宗教、民间宗教)。我的这本书突破了这一点,过去国内不少学者研究东巴教常常囿限在纳西族本身的历史文化、社会和宗教来进行研究的狭窄之弊,广泛地将东巴教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藏族本教、羌族原始宗教等做了深人的比较研究,还与藏传佛教、道教等也做了比较研究;对横断山区域即“藏彝走廊”地区纳西族、纳族群、以及藏族、羌族等民族的原始宗教现象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比较研究。
徐:你懂藏文吗?
杨:我不懂,所以我就想方设法搜集国外和国内翻译过来的藏文资料。研究东巴教,如果藏文好一些,那就更有利。我的这本书里有一章是专门研究敦煌古文献中的吐蕃文献与东巴教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弥补空自的创新。我是在阅读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书中有关于野马、马和耗牛等的传说中与东巴文献的惊人相似,于是进行了深人的研究,2006年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我的研究成果《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有很多反响,敦煌学界将它列为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一些敦煌学述评的文章都讲到了我的这个研究成果,我在此文基础上在《东巴教通论》中专章进行了论述,这也是突破以往研究东巴教局限在纳西族本身的一个案例吧。
徐:你刚才讲的确实是个创新点。
杨:它拓宽了研究敦煌学的视野,过去,很少有学者会想到敦煌学与云南有什么联系。
徐:一个西北,一个西南。
杨:我在《东巴教通论》中广泛地将东巴教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藏族本教、羌族原始宗教等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还与藏传佛教、道教等也做了比较研究;对横断山区域即“藏彝走廊”地区纳西族、纳族群、以及藏族、羌族等民族的原生性宗教(原始宗教)现象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比较研究。记得意大利学者、藏学权威图奇教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评论有“西方纳西学之父”声誉的洛克(Rock.J.F)的纳西学研究时,就提了一个观点,佛教传人西藏后,天长日久,藏族古代的本教逐渐地完全融到了佛教中,已经很难见到古本教在佛教传人前的原初面貌,现在可以在纳西族的东巴教中解开好多古本教之谜。
我在《东巴教通论》中专章对本教与东巴教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将唐代吐蕃本教对东巴教的影响了进行了论析。并花很大的篇幅对“东巴”与“本补”(也即本教巫师的自称本波)这两个纳西宗教祭司的称谓从语源、宗教等多角度地进行了寻根究底的考释。
这本书对东巴教中所反映的本土和外来神祇系列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对本土神抵谱系进行了深人的考证和梳理。为进一步深人研究东巴教庞大复杂的神祇抵信仰和神灵体系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我在书中还研究了东巴教独特的生命神“素”以及“威灵”和“威力”(“汁”)观念和“加威灵(力)”仪式。东巴教的“威力”(“汁”)类似于巫力,其内涵复杂和丰富,既包括了天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木石、老虎、耗牛、自鹤、雄鹰等自然物、动物的神秘力量,也包括了各种神抵、精灵、祖灵、酋长、头目、巫师、祭司等的威力,还包括了厉害的敌手、对手以及各种鬼怪的威力。
总之,这本书的好多篇章都体现了我一贯身体力行的“微观实证,小题大做”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比如其中有很多对具体宗教语词的考释,有对某个概念、某个神抵的考证。
徐:研究东巴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东巴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中非常有特点,是“活”的,又是旅游热点,知名度也高。你刚才讲的创新点也确确实实是创新点。我觉得这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藏传佛教融合了本教的一些东西,但它现在的面貌我们看不清楚。只能在纳西族的东巴教里去找它的原型。这对了解西藏藏传佛教的形成、内涵、底蕴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杨:我在书中也用专章对东巴教中长达10多米的巨幅布画“神路图”进行了研究,考证了其中一些属于古本教和藏传佛教、乃至婆罗门教的观念和内容,并分析了东巴祭司在丧葬仪式中用“神路图”中受外来宗教影响的观念对亡灵进行越过“鬼地”而超度到人界和神界的宗教法事,同时又根据纳西人传统的死后灵界观,把亡灵送到“祖先之地”这种二元并存的宗教观念。
《神路图》中有一幅图,上面画着长着三十三个头的一头大象,这是怎么来的。后来,我看到洛克等人的考释,认为这是来自婆罗门教的观念和内容。与雷电神因陀罗有关,大象的每个头象征因陀罗的一个宫殿。但是婆罗门教的这些内容怎么会出现在东巴教的神路图里,迄今还没有研究清楚,据洛克考证,藏族和蒙古族的绘画中都没有发现这个内容,而洛克在缅甸则发现了相类似的图。所以,东巴教实际上给大家提示了很多还需要解开的文化之谜。在藏彝走廊(或藏缅语族走廊)里,这种多种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徐:宗教的文化、经书,不是一两天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我觉得,你所做研究的价值不仅仅是你讲的这两点,表层的。从我的理解,你的《东巴教通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当中互动、交流、吸收、融合。东巴教和本教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西南的例子。本教本来是藏族的原始宗教,怎么会和纳西族的关系这么密切。
杨:在唐代,吐蕃派驻各地的军队里就有本教师,它把本教的文化也传播到了西南在吐蕃的势力范围。后来有的吐蕃赞普接受了佛教,就下命令,本教徒如果还要在藏区立足,就得阪依佛教。不然就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很多本教徒不想放弃信仰,就用马驮着经典逃到滇川毗邻地区丽江等地,然后把本教和本地少数民族的宗教揉合起来,形成了东巴教这个很独特的宗教形态。后来又融进了一些藏传佛教、道教等的内容。我在《东巴教通论》中也论述了唐代吐蕃本教对纳西人的影响主要是后期雍仲本教,而东巴教还与普遍流行在古羌人分布区域的古代本教还有着更为古老的同源异流关系,从本教和东巴教的神话传说看,东巴教中的居那什罗神山和美利达吉神湖崇拜与本教的岗仁波切神山和玛旁雍错神湖崇拜有密切的关系。
《东巴教通论》中也用专章论述了纳西人对东巴教认同的历史变迁,比如说到东巴教原来是纳西全民认同和信仰的宗教,随着明清时期汉文化的传人,东巴教的认同也随着纳西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发生变迁,比如说,过去丽江城区接受了汉学教育的不少读书人是瞧不起东巴教,把东巴象形文字也讥笑为“牛头马面”。清末丽江有个著名东巴曾经考上了秀才,可有些自视甚高的纳西读书人(读汉学的)竟然去县衙门里去抗议,说这个只会画牛头马面的人都要和我们为伍,这成何体统。这实际反映出一种接受外来文化后反过来瞧不起本族文化的认同变迁。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东巴文化研究热的兴起,特别是东巴经典列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以后,城里的市民对东巴文化的认同也逐渐改变了,春节贴东巴文对联的日益增多,堂屋客厅挂上东巴文书法字幅的也多了起来,东巴文字又成了一种时尚文化。
上世纪40年代,中国研究东巴文化的先驱、后来成为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李霖灿先生受中央博物院的委派到丽江去调研东巴教。他对丽江县鲁甸乡的大东巴和正才说,“你们的文化价值很高,你们写的东巴文是象形文字,不是牛头马面。”饱受文人讥讽的大东巴和正才激动得掉泪了,对他的徒弟们说,“你们听见没有,我们这个不是叫牛头马面,这是叫象形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东巴文化也经历了很多磨难,最初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直到改革开放后,通过国内外学术界正本清源的不断努力,才获得了重视。我个人对东巴文化的了解,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读大学后才逐渐深人的。
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我觉得你的研究也提供了典型的例证,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当中,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当中的互动、交流、吸收与融合。
杨:徐老师研究汉文化和汉民族通史。其实丽江就是一个文化在交流和互动中不断融合、形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例子。我土生土长在丽江古城。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后来我也研究丽江古城,写了几种关于丽江古城的书和一些论文。丽江古城在1949年以前,在全城2万多人口中,就有156个姓氏。1949年后又陆续增加了89个姓氏,差不多有217个姓氏。由此可以看到丽江古城民众来历的多样化。如今相当地道的古城纳西人,其中的大多数原来却有着汉族的血统,他们大多是在明清两朝来到丽江的汉族移民,后来与当地的纳西人通婚,久而久之就被同化为纳西人。如今他们虽然还会谈到自己的先祖最初来自“南京应天府”、江西、福建、安徽等地,但他们在说到这些家庭的历史时似乎是在讲述着一个遥远的,连自己也十分模糊的故事,他们的先祖很早就已经认同于纳西族。
如果追溯我的第一代祖先,他是明洪武年间一个汉族的移民,他叫杨辉,是个远近闻名的医生。纳西族民间普遍流传着“木土司三留杨神医”的故事,中央电视台还根据我这个祖先的故事拍摄了一个电视剧《四方街》。我曾写过一本《古王国的望族后裔》,写的就是我这个家庭,后来《光明日报》觉得我这个家庭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真实,还从中选了一部分刊载。
一个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的祖先杨辉相传是湖南常德府的一个名医。后来被木氏土司请到了丽江,家谱上记载他游学到滇。在丽江,他治好了本地包括霍乱等很多疑难病症,还治好了土司夫人的病。土司就不想放这个人才走,但杨辉想回家,执意要走。木土司就想了一个计谋,假装放他走,赠送给他很多的金银财宝,在他快要走出丽江的时候,就被木土司所派的一些装扮成强盗的壮士把他给抢了,一点不剩。他回去就没有盘缠了。只好回来见木土司,土司又慷慨地送他礼物,可又如法炮制把他抢了。到第三次,他就觉得和这个地方有缘了,天意不让走。于是决定顺从土司的挽留。木土司就给了他丽江古城大石桥下面的一块风水宝地,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他。他就留在了丽江。后来因为他“妙手回春,指到春生”,还被民间奉为药神。这就是丽江土司广纳人材,从中原引进人才的缩影。所以说丽江古城的纳西族的来历很复杂,我的祖先就是丽江古城最早的外来移民之一。后来他和纳西族一直通婚,就繁衍出了一个很大的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丽江一直从事的都是治病救人和教育的行业,如开设私塾教书。
从我这个家庭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以土司为代表的纳西民族非常开放,把各个民族的好东西都学过来。丽江古城的很多房子结构是中原汉式的,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祯认为丽江古城近郊的民居保留了“唐宋古风”。但纳西人在学习汉族建筑的同时,并不一味照搬,而是把本民族依山就势、随其自然,追求庭院宽敞向阳等传统融进了建城和营造住宅的理念中。你看,现在宣科先生领头的大研古乐队所演奏的洞经音乐(过去还有皇经音乐),都是从汉族地区传来的。有的音乐史家还认为其中保留了一些中原失传的曲目。纳西古乐里的《自沙细乐》,相传是“元人遗音”,一些蒙古族研究音乐的学者考证了“苏古笃”“伯波”等古老乐器是传自蒙古族的。“元人遗音”的来历是:忽必烈率领蒙古军在1253年“革囊渡江”经过丽江攻打大理,当时的纳西首领麦良觉得打不过蒙古军,于是采取与其和平相处的策略,亲自到金沙江边去迎接忽必烈及其军队,最终和忽必烈结成了好朋友,忽必烈走的时候就送了一个宫廷乐队给他。这个乐队就融合本地民间音乐,形成了今天的“自沙细乐”。从丽江的文化看,现在没有一种文化你可以说是100%属于这个民族原创的,。而大多数文化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融合而成的。其实从徐老师所研究的汉文化史中也可看出这种文化的融合。最典型的是文化上的盛唐气象就是不断容纳了“四夷五胡”后的文化而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汉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纳西族的东巴教也一样,其中有纳西、藏等民族的文化因素。

徐:讲到这里,我对你的身世很感兴趣,你能讲得更详细一点吗?
杨:好!我1955年9月17日生于丽江古城一个纳西族家庭,在丽江大研古城兴仁小学(现在叫丽江兴仁方国瑜小学)读小学、在丽江一中(现在的丽江市一中)读初中高中,然后上山下乡当了两年的“知青”,继而在丽江汽车运输总站当了一年的工人和一年的宣传干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因自己爱好文学,就读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期间,看书日多,眼界渐宽,渐渐沉湎于诸多自己原来不知的知识中,对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和纳西学等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除了选修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外,还登门向云南大学纳西族著名学者方国瑜、和志武先生求教,学习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纳西族历史、纳西拼音文字、国际音标等,1980年曾作为这两个前辈学人的助手,协助当时来云南大学进行有关纳西学学术交流的德国(西德)学者雅纳特(Janert. K.L.)教授工作了半个月,和他一起研究纳西语,用国际音标纪录纳西民间故事等。雅纳特教授在1961年至1962年期间曾是应邀到西德进行纳西文献编目和研究的洛克(Rock.J.F)博士的助手,1962年洛克逝世后,雅纳特教授继续长期从事纳西文献研究。和他的这次初步合作,是促成我后来到德国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契机。
徐:你的运气很好!这么早就与国际接上轨了!你做过田野吗?
杨:做过!读大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回乡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完成了毕业论文《纳西族的古典神话与古代家庭》,还写了《论纳西族(殉情)长诗“游悲”》、《纳西族人猴婚配神话刍议》等,这几篇论文后来在学术名刊《思想战线》、《民间文学论坛》以及民间文学刊物《山茶》上先后发表了,这算是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吧。
徐: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的?
我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了一年,有机会跑了云南的不少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有幸的是1983年1月,我获得德国(西德)国家科学研究会(DFG)学术基金,应雅纳特教授之邀,到德国科隆大学与他进行合作研究,1985年1月返国,在1986年3月至1988年3月又再度赴德国科隆,完成了 “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著作4种,《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曾对此作了相关报道,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走出国门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少数民族学者,”当时出国不易,看来我确实算是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出国进行民族文化合作研究的少数民族学者。
徐:真是好运连连!
确实,在德国的4年治学岁月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的根和生命是在自己的故土,他的使命也是扎根在故土,与故土休戚与共。因此,我无心恋异国繁华,回到母亲之邦,开始了我走向田野,进行民族学、纳西学研究的漫漫治学路。我后来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后,又在职攻读了云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
徐:看来你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志气的人!下面请你谈谈你从事民族研究的具体情况好吗?
杨:好!到2016年,我从事民族学研究已经33个年头了,在这33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而对纳西学所下的功夫最多,多年来,我跋山涉水,漫游于高山深峡,山村农舍,深入纳西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走遍了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丽江县的大部分乡镇,也多次深入到迪庆州的纳西族地区、以及四川省的一些纳人的居住区以及西藏昌都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这些深入山野村寨的田野调查使我获益匪浅,如果没有这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我就不能写出如今已经问世的这些著作和论文,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样长期的田野调查,我也不可能对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和当代变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三十多年来,我立足云南这块红土地进行研究,在以纳西学为主攻方向的民族学领域里取得了一些成绩。迄今,我在国内外已经出版了33部专著,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新华文摘》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其中10多种论著在美国、英国、德国、荷兰、印度、泰国等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和学术论集中发表,如我1988年在德国波恩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现代纳西文稿语法分析和翻译》第一卷;1999年,我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汉尼(Feuer.Hanny)合作,在基于半年的田野调查上写成的长篇学术论文《云南藏族和纳西族的问候语研究》,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藏缅语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主办)上发表,此外,我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英国、德国、瑞士、荷兰、印度、泰国等国学术刊物和学术论集中发表,包括国际学术权威刊物——《藏缅语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主办)杂志、瑞士苏黎世大学出版的《纳西、摩梭民族志》、德国伯尔·巴德(Ball Bod)科学院出版的《原住民传统知识体系研究》、英国赛奇跨国出版公司出版的《两性、技术和发展》、越南河内出版的《云南民族学文集》等,收到国外同行的好评。
除了学术研究,我看重一个民族学者与社区民众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维系和学者对社区民众的道义、良知和责任感;看重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对社区民众的“回报”情结。因此,除了致力于民族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也积极参与关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尽己所能地为当地社区民众办实事,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各种国际合作的社区发展研究,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作田野调查,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与国内外同事一起促成了丽江纳西族农村的一些合作经济实体;争取国际资金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人培养和乡土知识技能培训、在乡村小学里进行参与式的乡土知识教育等方面的项目,完成了“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的实践和研究”、“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乡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培训”、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在丽江民族中学读书等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社会影响。现在玉龙县白沙完小的乡土知识教育和少年足球队等在全国都产生了影响。
曾以几句诗表达过自己治学迄今的一点心怀,这里给徐老师看看:沉潜学海三十载,寻径问学度华年。跋涉山乡访野老,探究鬼神游大千。也曾漂洋会同道,论剑学术在讲坛。鸿泥雪爪是旧迹,海阔天高望远山。
徐:很好!有激情!这是你取之不尽的学术源泉。
杨:因此我觉得,一个本土的少数民族学者的研究,不要囿限在本族的视野里,不要陷人那种论证纯而又纯的原住民文化的怪圈中,不要陷人论证一切文化皆起源于某地某族而在学术上走火人魔。象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学者,在研究中要做到聚焦本族,熟悉本族,把田野调查等作扎实,但又要学会能跳出本民族,冷静地旁观和鸟瞰本民族,通过认识其他民族特别是在族源和文化上和本民族关系密切的民族来认知本民族,客观地去发现它,研究它,而不要老想着把本民族的文化说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或者是想把什么内容都说成是自己本来就有的,忌讳说是外面传入的。使学者的研究失去客观性和真实性。
徐:从你的讲述中看,丽江古城的文化如果只讲本上纳西人,那就说不清楚。
杨:是的,那是不可能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太多了。不过,丽江这个案例有意思的是,汉族移民进去以后,在语言和服饰等方面就被纳西人同化,人乡随俗,但他同时也把各种汉文化带了进去,纳汉文化就这样逐渐融为一体,真正变成了相互的同化。而在云南很多地方,多是当地少数民族被汉族移民逐渐同化,有的连母语也逐渐失去了。
而丽江的情况是,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只要你是住在古城的,自然就会说纳西话,我很多居住在丽江古城的汉族同学都会讲纳西话。但是如果你是居住在丽江古城外围的机关单位里的汉族,就大都不会说纳西话,因为他每日朝夕相处的多是本族人,说得多是汉话。
从丽江古城的发展史看,说明一个民族的发展确实要广采博纳,多多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如果本民族自负或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那么,当年本教文化、汉文化以及藏传佛教等进人丽江的时候就会遭到排斥,这就不可能形成丽江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
徐:杨教授你研究的价值很重要,说明了费老的多元走向一体过程中的交流互动和互补。纳西东巴教的形成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样本,你能很清楚的分出哪些文化是本民族的,哪些文化是外来的,如藏族和汉族的,文化层很清晰。纳西族的研究,生生不息,十分深入。今天得到您赠送的《东巴教通论》,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你将纳西族的研究推向了深入。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非常赞成和欣赏您的研究。很多本民族的学者往往抱着“一棵树”主义,而忽略了多看看和这棵树相关的森林和环境,有些陷入民族中心主义。
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汉族的历史在早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构建,黄帝也是一种建构,黄帝是四面的,炎帝是牛头人身的形象,现在说岂不是妖怪?那时候允许汉族的儒家的精英们把黄帝和炎帝进行构建,现在要构建一种部落首领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政府把它作为一种产业打造,这个值得思考。学者本身如果能跳出本民族的圈子站得高一点去看我们周围的事物,包括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和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接近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类学家。
徐:但是我们能理解他们建构祖先历史的心理和需要,无论他们是怎样的心理和需要,一方面我们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要指出这就是一种建构,无论怎么搞,我们还是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把它放到恰当的位置。
杨:学术的底线是必须要尊重事实,要客观。如你所说,因为有复杂的历史因素促成了当下的各种建构。比如为了发展旅游,吸引游客而到处建构祖先传说人物故事景观来历等。但是作为人类学家应该面对真实尊重事实,不能随波逐流。
徐:对,站高一点,能跳出来。
杨:比如“东巴”这个词本身是藏语过来的,但是有的纳西学者为了论证这是纳西族本土的,就望文生义地附会了不少意思。很多当下的文化操作,就是为了一种功利目的而建构,为了证明这就是某族的本土的,地道的,千方百计要说成与其他文化没关系。其实从人类学的观点看,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外来的成分是常态,这并不影响其价值,相反还可以证明这个民族文化的丰富性,说经这个民族善于学习吸纳其他文化,因此才有活力。如果是封闭的话,丽江古城没有办法产生,也不会有东巴教。
另一方面,我们从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发人深思的东西,比如纳西族妇女从来没有缠足的传统,汉族移民到了丽江以后,人乡随俗,学纳西族妇女一样不缠足,免去了很多痛苦。这就是一种文化互惠的关系,在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徐老师研究汉文化也会发现,汉文化进人到不同的地方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不断吸收,有的还是很好的吸收。比如丽江的民宅,纳西人的建房理念是认为院子要宽敞,要向阳,满地阳光,多种花草,堂屋外面要有供人日常休闲的宽敞的厦子(走廊),来自中原的汉式民居就与这种地方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与那种讲究财气内蕴、天井窄小的汉式住宅截然不同的风格。比如,丽江古城和大理不同的是,大理古城是四四方方的,受了“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中原建城礼制影响。而丽江古城则在形成过程中始终保持了随自然地理营建城市的思路,即“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随其自然方式。因此当今建筑学家认为大研古城所始终保持的自然形态平面,是本土文化的自尊、自信的胜利。汉文化进来后产生了一种融进本土理念新的文化。我想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应该是这样的。即国外的东西应该接纳,但不是照搬。
徐:呵呵,确实,丽江妇女的天足之俗,与汉族封建文化中对妇女的苛求截然不同。
杨:民间相传明代状元杨升庵在朝廷获罪而被贬到云南,他在云南其实过得挺好,民间传说他常常头插鲜花,游乐山村城郭,吟诗喝酒,广交各路贤达和少数民族朋友。杨升庵作为罪人被贬后反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他找到了很多在中原礼俗中找不到的东西,其中不少就是人性的自由和率性而为的民俗。人类学家去研究这些还是蛮有意思的。不同的文化碰撞之后可能更有利于新的思维的产生。盛唐时的汉文化为什么激发出那么大的活力,就是一样的道理。文化是在一体化过程中的相互吸纳、互补、共生的。我的研究是根据事实,不会去刻意建构。搞学术研究就是要客观。而文化产业是另外的路子。
徐:我现在要讨论你的第二本代表作《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此书是4O多万的大作。尤中、李绍明、王尧先生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请您对此书做简要介绍。
杨:过去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论著相对比较多,而且多偏向于研究蒙藏、汉藏、汉蒙等大的民族。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少,我因此选择了纳西族和藏族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则基于历史上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的丰富多彩。明朝的时候,由于明廷将丽江视为“西北藩篱”防范吐蕃,木氏土司又积极扩展统治领域,因此战事比较频繁。两个民族在数百年中相互打了很多的仗。但是纳藏两个民族却没有因此成为世仇,而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长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丽江成为纳藏贸易的重地和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重地。近期中央电视台一频道和八频道都热播的《木府风云》,其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反映了民族之间如何化解历史上的仇恨和矛盾。历史上,木氏土司很尊重藏族的风俗,花大量的钱帮助藏族建盖寺庙。著名的四川理塘大寺就是丽江木土司出钱建造的,还请了三世达赖来开光。明代好几个重要的藏传佛教噶举派活佛包括噶玛巴(大宝法王)都与丽江和木氏土司关系密切。噶玛巴十世却英多杰因为清初格鲁派和噶举派教派之争而避难丽江,在丽江生活了33年。今年在纽约召开了一个研究噶玛巴十世的专题国际会议。原来还拟举办一个噶玛巴十世留在丽江的一批唐卡画展览。丽江在明清时期是噶举派的重地,木氏土司是噶举派的忠实信徒。噶玛巴十世在丽江弘扬噶玛噶举教派。滇西北十三大寺都是噶举派的。
木氏土司还主持在丽江印制了藏区第一套卷帐浩繁的大藏经“甘珠尔”,现藏于大昭寺,是该寺的镇寺之宝。这套大藏经曾辗转收藏在理塘寺,因为称为“丽江理塘版大藏经”。纳西族和藏族商人在商贸交流方面也源远流长,非常默契。藏商一般到了丽江就不再往前走了,因为他们在语言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不太适应与汉地商人直接经商,所以他们多把物资在丽江委托给当地的纳西族商人出售,并为他们买回需要的茶叶等货物。丽江既是茶马古道上货物的重要起点站,同时也是个终点站。丽江古城纳西人和藏商还形成了很有特点的“房东贸易”,双方建立了良好的诚信关系,即使有些货物一时滞销,纳西房东也最终会将货款如数给藏商。因为纳西人认为藏人直爽坦诚,因此,丽江束河的纳西族还常常请藏族人为他们管理村子的山林。我在这本书中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汉藏文献和外文资料,研究了纳藏两族历史上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商贸等诸多方面的交往,还把我多年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与文献有机融合,其中有不少我在纳西族地区和藏族地区调研的个案。就滇川藏毗邻地区而言,我们还可以深人研究很多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历史关系。这里不乏很多对当前建构和谐民族关系可以借鉴的历史智慧呢。目前藏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也比较高。
徐:民族之间打战却没有结为世仇的原因是什么?
杨:因为双方在打战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化、宗教和商贸的交流。木氏土司移民到如今的迪庆和四川的巴塘理塘等藏族聚居地,但并却没有把原住藏民都赶走。大家住在一起,慢慢的互相适应,互相学习。木氏土司把水利技术和各种种植技术输人到藏区,建造寺庙,互相通婚。一个民族在战后通过尊重对方的文化和信仰,通过加强有利民生的经济交往,逐渐化解了战争的创伤。纳西族记载在东巴圣典中的《创世纪》中说:纳西族、藏族和白族是一对祖先育出的三兄弟,就是这种友好关系的最好的说明。
我在学术研讨会上听新疆的学者讲到,新疆的维族和汉族的关系在上世纪50,60和70年代还是很和谐的。我们需要寻找历史的经验和积累的智慧来研究当前的民族问题。这也是我这本书中的大量篇幅所透露出的历史信息。
徐:战争的交往是不是使得双方的交往更深入?
杨: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因为战争导致的移民等使两个民族的交往加深了,民族在迁徙过程中摩擦又有交流,交流的形式有和平的形式,也有冲突的形式。在磨合和相互沟通的过程中,战争与摩擦会越来越少,大家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各方面都有密切的相互交流,于是也逐渐形成了在宗教信仰、文化交流和商贸交流方面互动互补、相互包容的局面。比如这本书中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大东巴的父亲和作为宁玛派活佛的儿子各自信奉自己的宗教,但在宗教祭祀上有杀生观念方面的冲突,东巴认为祭神驱鬼,要用祭牲才会灵验,但是儿子认为不应杀生。后来父亲在仪式中的杀生慢慢减少了。滇西北的纳西族与藏族都有相互请对方的宗教专家举行特定仪式的习俗,东巴和藏传佛教僧人各司其责做仪式,这是相互尊重对方的信仰与文化的结果。
徐:宗教对精神方面的影响可以定民心,是吧?
杨:明朝时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战争比较多,清代以后,两族之间在宗教、文化和商贸交流方面加深。各地藏民每年朝拜佛教圣地鸡足山,首先要去丽江的文笔山上“借钥匙”(相传释迎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摩诃迎叶尊者把钥匙留在这里了,因此要借钥匙)才能打开鸡足山之门。藏民要一路化缘来到丽江,丽江纳西人都会给藏民朝山者好的食品。
纳藏两族民众之间的通婚也比较普遍,两族聚居一地的也比较多。两族相互之间非常信赖。我听有的马锅头讲过,过去纳西跑茶马古道的赶马人沿途去藏族寺庙中借钱粮等物,僧人二话不说就会借给你,我的书中也记录了类似不少佳话。
徐:藏族和纳西族在经济上应该是有紧密联系?
杨:各种纳西地区和藏区的土特产之间的交流互补,各种工艺和农业技术的交流,饮食的交流等等,宗教人士也借助茶马古道做交流,僧人进藏学经朝圣和茶马古道上的商人一起走比较安全,因此常常结伴而行。
徐:您的研究的现代价值可能在思考当代我们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时会凸显出来。
杨:我现在在思考为什么云南的藏区能保持稳定发展?云南的藏区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和多民族有交流交往的稳定基础,现在政府各级部门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固然也很重要,但这种和谐局面也得益于过去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形成的格局。这个对政府的施政应该有启示性。
徐:您的研究之所以水平高,是因为您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的学者,而不单纯是某一个民族的学者。当然这个也与您的求学经历有关。
杨:我是1955年出生在丽江古城。在方国瑜兴仁(民间称大佛寺,因该校原址是一个汉传佛教寺庙)小学读书,老师是用纳西话和汉语进行双语教学,读小学时汉语说得很差。普通话是读高中以后才慢慢学习的。高中毕业后当知青两年,之后分配到丽江汽车总站当修理工,后当了一年宣传干事。因喜欢文学,高考恢复后考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后来发现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的研究人才。自己在大学接触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于是选修了民族民间文学课程并当了课代表,后来发现民族民间文学离不开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于是又选修了宗教学、文字学、民俗学等课程。我的兴趣就慢慢转移到了民族学人类学,后又跟随方国瑜先生与和志武先生学习东巴象形文字等。1980年,德国(西德)的一个学术代表团来云南大学访问。其中有洛克唯一的学生的雅纳特(Janert.K.L)教授,他也是季羡林先生在德国读梵文时的同学。他专门来和方国瑜先生、和志武先生交流。我被方国瑜与和志武先生推荐作为他们的助手,和他一起工作了半个多月,把我用国际音标记录的几个纳西故事讲述给他听。后来他执意邀请我到西德去访学。1983年一1988年期间我先后两次在德国访学了四年,其间不仅把英语练成能用来一起做研究,还一起完成了“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著作4种。
雅纳特教授原来是梵文专家,他在1962年开始对东巴经典感兴趣。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的所长图齐(G, Tucci)是国际上的藏学权威,他意识到洛克所作的东巴文献的研究的价值,他对洛克的纳西文化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为他的论著所写的序言中多次称洛克为“伟大的学者”。他认为纳西文化在宗教学、民族学的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上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国家图书馆动议购集已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东巴经。在阿登纳总理的支持下,以昂贵的价格把洛克原先赠送给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的500多册东巴经悉数买回。当时,该研究所急欲出版洛克的《纳西一英语百科词典》两大卷,但苦于资金短缺,只好忍痛割爱,卖出经书筹资。联邦德国国家图书馆随后又从洛克那里得到他个人收藏的1700多册东巴经原本及照相复制本。1962年1月,洛克应邀赴联邦德国讲学和编撰东巴经目录及经书内容提要。雅纳特(I},L,lan-ert)博士协助洛克从事编撰工作。至1962年10月,编订和描述了527本西德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东巴经,编撰成《德国东方手稿目录》第七套第一部《纳西手写本目录》一、二卷。编撰工作尚未完成,洛克不幸于1962年12月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去世。雅纳特继续进行西德所藏东巴经的编目工作,完成了《纳西手写本目录》三、四、五卷。
德国人在他们的经济处于非常困难时期的上世纪60年代初就由总理亲自支持以巨资购买东巴经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反映出德国人一种文化上的世界眼光,珍视世界上的历史文化遗产,德国学者常常和我谈起,像东巴经这样珍贵的文献,无论是那个国家那个民族创造的,都是人类的瑰宝。
我在德国是做合作研究,因忙于工作,没能读学位。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过3个月的博士后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参加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比较多,先后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进行过关于丽江玉龙雪山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合作研究,关于抗日战争期间闻名遐迩的中国“工合”(工业合作社)的历史和在新形势下重建农村合作社的研究;关于藏族和纳西族问候语的研究等等。从1999年以来的几年间,我参加云南省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的“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国家大河流域公园)”,作为丽江地区的课题组组长,和同事们先后调研了近20个纳西族和彝族的村落。其间我还担任了2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项目的文化顾问,与国外学者展开广泛的交流。记录了这期间我所做工作的研究成果有《策划丽江》、《云南玉龙山区域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调研》、《云南藏族纳西族的问候语研究》等。
我在20多年来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汲取了不少国外同行的治学方法和经验。1995年至1996年,我获得联合国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UC.Davis)分校研究访问;多年来,我先后应邀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瑞典国立远东文物博物馆、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亚洲部、德国斯图加特巴德·伯尔科学院、瑞典伦德大学、亚洲理工学院、加拿大西门大学、美国多个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还曾经到加拿大卑斯省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学术考察。2003年在美国惠特曼学院的首次“亚洲文化教育年”期间,为美国学生开始了半年的《中国西南的民族性与现代化》(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of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ernChina) ,《中国纳西族的文化艺术》(TheCulture and Art of Naxi People of China)等课程,受到美国学生的好评。期间还与该校人类学系主任孟彻理(Chas Mckhann)教授合作出版了一本《图像及其变化一东巴艺术中的再想象》Icon and Transformation: (Re)Imaginings in Dongha Art
我觉得我们治学,了解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结果很重要,所以,我还花了很大功夫,翻译了一些国外纳西学论著,主持审校和重译(部分)了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博士研究纳西族的重要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由于此书很多正文和注释需要核对大量汉、藏、纳西文献以及外文资料,还有不少植物学词汇进行重译,因此,审校这本书所花费的功夫是相当大的。近年来,我还组织翻译了当代国外纳西学名著《纳西、麽些(摩梭)民族志》( 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
从我的研究而言,对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冲突的深人研究成果是研究纳西族殉情习俗的三本著作,最早的一本是《神奇的殉情》,此书1994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来也在台湾出版了。2000年在深圳出版了一本《殉情》,列人“人类学田野”;一本就是2008年出版的《玉龙情荡—纳西族的殉情研究》,列人了尹绍亭先生等主编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系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这本书入选了“2014书香中国”300位名人名家推荐300本好书”之一)。
我在此书中增加了很多田野调查资料,增强了理论分析。我关于殉情研究的书的有关章节也在国外出版了英文版。这本著作分析了主要由政治制度和文化变迁引发的纳西族的殉情悲剧,这是一本研究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殉情这一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著作。这本书基于大量案例主要提出的观点是:当主体民族(清代时)以一种大文化沙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边地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时,边地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就被认为是野蛮鄙陋的文化,要加以“文明的改造”,结果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大冲突。丽江在1723年改土归流之前,纳西人的恋爱是相对比较自由的,不少地方即使未婚怀孕、有私生子都不会被社会蔑视。但是清代极端异化的儒家三纲五常被强制地实施。按清代的法规,当时藏族如实施天葬就要被凌迟处死,非常严厉。纳西人的火葬习俗也被认为是陋俗而强行制止,按纳西人的生死观,不火葬灵魂可是回不了祖先之地,这是很可怕的事。因此纳西族抗争了100多年,慢慢才在一些接受了汉学教育的纳西文人带头,才慢慢接受了土葬。现在政府又号召要火葬,接受土葬习俗几百年的不少纳西老人又想不开了。在昆明的一些老人特别害怕呆在昆明,说担心自己被火葬,老了以后还想着赶紧逃回丽江葬在祖坟上。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习俗可以因为一种强力的文化沙文主义压迫和政治改造而被彻底异化。
1723年“改土归流”后,各种压制妇女身心的制度也实施到了丽江纳西族中。这些外来观念和本土习俗杂揉成以一种“婚前恋爱自由,结婚则不自由”的习俗。青年男女在婚前的恋爱是自由的,这是沿袭了的传统习俗,而婚姻则要完全听父母之命。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加上对妇女的各种限制,比如清代还有各种限制妇女参加元宵、灯会等的限制。很多妇女就觉得这世道太难了,这些社会因素加上纳西人的宗教信仰因素,比如基于“祖先之地”信仰的“山中灵界信仰”,产生了一个俗称“玉龙第三国”(舞路游翠郭)的山中灵界,那时殉情者的世外乐园。殉情者相信他们殉情后可以去到那里,在那里可以骑着老虎到处跑,有自鹿来为他们耕田,锥鸡为他们啼明;他们可以用彩霞来织衣服;这里人不会老,青春常在等等。社会因素和信仰因素一综合,于是就有了殉情的诱导因素,纳西人中就产生了大量的殉情悲剧。丽江曾被称为殉情之都。殉情者自杀前要浓妆盛服,歌舞唱酬,要选一个能见到玉龙雪山的风景优美之处殉情。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殉情》一书用了田野实录和文学化的写法,有较强的可读性。
此外,我还出版了《纳西族文化史论》(此书获“第十一届云南图书奖”二等奖;《纳西文明》(此书教育部推荐为《历史》(高一年级第一学期)教学参考书),等十多部纳西学研究专著。
徐:你是哪一年博士毕业?哪一年结婚的?
杨:我是1999年博士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当时我已经是研究员,并人选了“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但是觉得还是要多学些知识,特别是我功底比较薄弱的历史学应该恶补一下。就在职读了博士。我是1983年出国以前结婚的,回来时我的女儿已经有两岁了。我爱人也和我出去了一段时间。我回国时预料女儿会认生,所以在德国买了一个台湾制造的粉红色的电动玩具小猪,动起来会叫还会惟妙惟肖地用鼻子拱人。呵呵,果然女儿咋见到我,有些怯怯的,不肯喊爸爸,给了她粉红色的小猪,一动一叫,小孩可高兴了,也开始喊我爸爸。我爱人家是汉族,是从丽江邻县永胜在上世纪移民到丽江古城的。他们家在家里是父母讲永胜汉话,而兄弟姐妹之间则说纳西话。我妻子精通纳西语,她讲话的纳西口音比我还重呢。她可以说是最后一代在丽江古城被纳西人同化的汉族吧。现在的丽江特别是像古城这样的区域,则又面临着纳西人要被逐渐汉化的趋势。我们夫妇在昆明常常和女儿说纳西话,并要求我的女儿和她祖母通电话说话只讲纳西话,因为我母亲听到纳西话会很高兴的。所以,我女儿是当下在昆明长大的纳西年轻人中还能讲纳西话的少数人了。她会讲纳西话,而她的普通话比我标准,英语也不错。这证明年轻人学习多种语言并不相互冲突,倒反对思维和学习语言有好处。我写的《古王国的望族后裔》这本书中,就讲了不少我这个纳汉合璧的家庭的不少故事。也算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家庭的案例吧。我个人认为民族是个文化的概念,不适合用基因等来论证。
徐:民族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在中国通过民族识别出来的56个民族,又被赋予了政治性。
杨: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民族的融合与分化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变化。我在藏区看到,因为藏区有对藏族的优惠政策,一些纳西族逐渐倾向于报自己是藏族。而在丽江,也有因为丽江和纳西族当代的文化名声和经济上的发展,填报自己为纳西族的年轻人也在增加,特别是那些父母一方是纳西族的。一方面,很多纳西人在致力于推动传统文化包括母语传承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已经日渐生疏了母语等自己的文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学者,我现在思考得较多的是少数民族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继承上,也广泛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基于母亲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上再创当代的文化。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是流动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应该增加原创的内容。但关键是要保留自己文化的个性特点,保持自己的魅力,不应随波逐浪地被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被彻底同化了。
徐:除了上述很多继承研究,看来你还在应用性研究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杨:是的,除了学术研究,我看重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学者与社区民众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维系和学者对社区民众的道义、良知和责任感;看重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对社区民众的“回报”情结。因此,除了致力于民族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也积极参与关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尽己所能为当地社区民众办实事。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各种国际合作的社区发展研究,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作田野调查,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与国内外同事一起促成了丽江纳西族农村的一些合作经济实体;争取国际资金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人培养和乡土知识技能培训、在乡村小学里进行参与式的乡土知识教育等方面的项目;完成了“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的实践和研究”、“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自沙乡自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培训”、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在丽江民族中学读书等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社会影响。
徐:纳西学是你的学术重心,除此之外,你在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下功夫较多?
杨:除了纳西学,我还从事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我的民俗学专著《灶与灶神》,是对中国的灶神信仰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研究的一本专著,在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很快重印,1996年在台湾汉扬出版社出版,2000年在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
我主笔的《火塘文化录》是《灶神研究》的姐妹篇,此书从民俗、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首次对过去无人论及的中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火塘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析,应该算是一本以小见大的拓荒创新之作。《中国社会科学》曾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由于此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曾两次重印,并于2000年再版。该书还在1999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译成英文。此专题系列论文之一《论火神》被《新华文摘》转载,并人选由中国科学院编的《中国八五科学技术优秀成果选》(1990-1995)一书中);该文亦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1993一1995年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此外,我还出版了一些田野纪实类的图文长卷散文,比如《寻找祖先的灵魂》,先在台湾出版,后来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又出了大陆版;还有《西行茶马古道》,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灵境丽江》,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版,《杨福泉作品选集》,光明日报出版社版。
老照片学术画册《远去的背影一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人选“首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这本书虽然很贵,但早就卖完了。不少国外学者向我打听,问这个书会不会出英文版。现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来组织把它翻译成英文,我正在筹划中。这本书设计很有水平,书里的很多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70年代,这期间反映中国少数民族状况的照片在国外很少。照片很清晰,并且按照民族分成一组一组的。从这个书可以看出来,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派出的民族工作队的工作做得很细,里面有很多难忘的历史场景,此书有图有真相,很有历史资料价值。我在编辑的时候,要求撰稿者尽量把图说做得细一些,这样信息量也就比较大,能了解到照片后面的很多背景内容。
徐:谢谢您接受采访,非常感谢!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