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原文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摘要]二十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关键词]格尔茨 民族志 《爪哇的宗教》《尼加拉》
一、从“记”到“写”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学术界一直在“转向”的漩涡中寻觅新的出路,此时的人类学也同样面临着一个“认识论转向”的问题,即人类学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人类学家们逐渐发现人类学知识与权力、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多样性以及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惘然于世外桃源般的“特洛布里恩德岛”的不复存在,于是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共谋等概念和理论相继出现。八十年代中期,这些反思汇纳到对民族志文化批评的洪流之中。如果说二十年代的人类学正处于实证主义的浪尖,那么五十年代进入人类学殿堂的格尔茨恰好处在两座巅峰的正中。
1922年,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的付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纳入社会科学的王国,在实证主义的大旗之下所开创的正规人类学训练要求学生到一个陌生的“那里”(there)记录(record)下见闻,再回到这里(here)用民族志的形式客观地呈现“那里”的整体文化;为了寻求客观性,民族志作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淡出民族志文本之外。[1]16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格尔茨提出解释人类学理论,“文化”转向了意义体系;他还指出,民族志所呈现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文化还包括人类学者对“那里”生活方式的渗入。[1]8我将实证主义时代的民族志写作模式概括为“记”,解释人类学理论下的民族志写法归为“写”,对应于格尔茨所言的“浅描”与“深描”。
“书”皆由人所为,我们将作书的人称为“作者”;作者与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有的情况下,书的内容与作者无关,作者只负责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进而进行一些整理与分析;而另一种情况则是书的内容乃作者所创。福柯将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文类分为科学与文学,并认为科学属于前一种情况,而文学属于后一种。[2]141-60从写作模式的角度,我将第一情况总结为“记”,第二种情况归纳为“写”。八十年代的格尔茨认为人类学更偏向于福柯所划分的文学类。[1]8
“记”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记”的观念肇始于孔子,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述”指对已存在事情的转述,相当于“记”;“作”,包含秉笔者的创造性,相当于“写”。司马迁在《史记》中继承了孔子的这一主张,他确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考订标准。[3]这一主张到了汉代被扬雄与班固总结为“实录”;扬雄在《法言·重黎篇》中有言:“或曰:《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班固对“实录”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2752可以看出,孔子的“述”到了汉代已不仅仅是对已有之事的转述,还可以包括恰当的道德评判,史官可以对历史做有意无意的选择与删略;但有趣的是,秉笔者的主观意愿仍然是要被抑制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所言:“左右,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可见,“记”始终排除秉承者的创作。
写(write),相当于孔子所言的“作”,在作品中突出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或者作者意图(authorship)。福柯将作者与作品的这种关系称为“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格尔茨认为有必要在民族志中再次强调这种“作者——功能”,这是建立在他对实证主义时代民族志的反思之上的。实证主义时代的民族志为了追求客观性而取消了作者的主体性,文化变成了自在的客观性知识,民族志作者则成了知识的技工(the mechanics ofknowledge);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将人视为客观对象,犹如制图员一般的呆板描述最终会导致种族中心主义[1]8。对于格尔茨而言,强调“作者——功能”实际是在强调人类学者的“在那里”(been there)以及自我与他者的意识。民族志不是客观记录,同时也不是文字游戏。
格尔茨说道:“‘民族志学者是干什么的?’——他写作”[5]19,格尔茨特别强调民族志写作中的自我呈现。他认为传统的“参与性观察”恰恰因为缺乏这种自我意识而认为眼睛所见即为事实。“写”所强调的自我呈现在格尔茨这里蕴含着两个向度:民族志本质上是人类学者对特定文化(特别是象征符号体系)的一种解释,同时人类学者还必须对自己的角色以及“我文化”有一种自觉,以防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
格尔茨在人类学上的成绩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志研究,再就是他所提出的解释人类学理论。[6]378-413在其有关印尼研究的民族志当中,《爪哇的宗教》是起点,《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下文简称为《尼加拉》)则是顶点。[7]1137格尔茨初入人类学之时,正是马氏所树立的现代民族志范式方兴未艾之际,彼时的正规人类学训练就是要求研究者到“那里”观察、记录自在的“文化”。《爪哇的宗教》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记下了爪哇社会中纷繁的宗教文化。八十年代,正是“写文化”即欲驰骋疆场之际,一股后现代之风迫在宣告“记录”时代的结束。自始至终与后现代保持距离的格尔茨,其《尼加拉》却极为漂亮地展示了“写”的魅力;同时也体现了格尔茨关于民族志的观点。从《爪哇的宗教》到《尼加拉》清晰地显示了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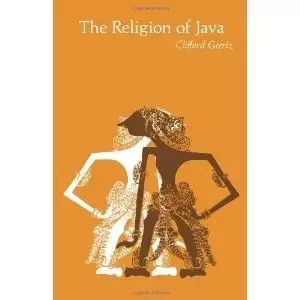
二、从《爪哇的宗教》到《尼加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格尔茨考入由帕森斯与希尔斯主持的哈佛社会关系系,跟随克拉克洪学习人类学。[8]101952年,格尔茨通过导师的一个项目进入他生平的第一个田野点——爪哇的湃尔(Pare)。格尔茨在入学后通过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而着迷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因此克拉克洪建议他在该项目中负责爪哇宗教方面的调查。这次调查的成果便是格尔茨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爪哇的宗教》。
1942年搏厄斯辞世之后,五十年代的美国人类学实际上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还是仰首期盼大洋彼岸吹来的思想菁华。这时由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共同确立的现代科学民族志范式仍然是美国人类学所遵循的典范,所以格尔茨和他的同学们都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想象为寻找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特洛布里恩德岛”的浪漫之旅。[9]106马氏和布朗通过各自民族志代表作所开创的“科学”民族志文本风格被后人概括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民族志的要义是作者尽量隐身,以描述的客观来支持方法的科学,以对生活的诸方面的详细描述形成生活的具体感,并指望细节的积累能够转化成‘社会’的总体面貌”。[10]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记”必不能含有秉笔者的创作,这反映在实证主义时代民族志中便是“作者意图”须淡出文本之外。民族志就是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对文化的记录,这背后潜藏着培根的科学认识论。那时关于文化的定义仍然在泰勒的“复杂整体”中打转,文化被划分为诸多事项,人类学家相信眼见必为实,认为通过直接观察必然可以获得有关各种文化事项的知识,当这些知识足够全面时便可以达到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认识。正如史官可以在记载的过程中作出些许道德上的批判或对历史进行一些删略,实证主义时代的民族志作者也可以选择在文本中进行一些分析,但这类分析犹如对科学试验的解析,显然不是作者意图的显现。
所以,格尔茨美国五十年代的民族志训练模式归纳为“观察——记录——分析”。[5]20格尔茨所参与的克拉克洪的这个项目将爪哇的社会文化划分为村庄生活、农业经济、市场、行政组织、家庭组织以及华人社区等,项目组成员分别负责其中一个专题。格尔茨的调查报告(《爪哇的宗教》)于1960年最先得以出版,格尔茨也藉此获得博士学位;项目负责人奥利弗(DouglasOliver)在该书的出版序言中指出该书之所以最先出版是因为它在呈现巴厘生活方面做得最好。[11]vii
《爪哇的宗教》这本民族志完全按照“观察——记录——分析”模式完成的。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前三部分详尽描述了三类群体的三种宗教,最后一部分是理论分析与总结。整本民族志都是在围绕爪哇的各类宗教信仰及仪式进行记录、并沿用韦伯和涂尔干的观点加以分析。单从篇幅上看,全书的基调也是以描述为主的。
格尔茨发现爪哇存在三种宗教信仰,而这三种宗教又恰好对应三种社会结构:村庄、市场和官僚制。韦伯将世界历史中的宗教分为两类:“传统的”与“合乎理性的”。前者指“原始民族”的“巫术”信仰,趋近于泛灵论;后者指具有严谨体系的信仰,诸如犹太教、儒教以及印度教,神不再充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前者更为注重仪式,后者则偏向于信仰;而理性化宗教的一大特征便是具有较为完整的组织机构。格尔茨藉此划分了爪哇的三大宗教,这体现在篇章的安排上:先是农民的宗教传统,格尔茨称之为泛灵论;接着是具有现代色彩的伊斯兰教,最后是泛灵论在新兴城镇中的变体,主要延续印度教传统。后两类宗教近乎韦伯所言的理性化宗教。
格尔茨尤其对商业阶级中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浓墨重彩,其实他有意将这种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与韦伯所言的新教类比。后来他也提到自己受韦伯的影响一直关注宗教信仰,特别对伊斯兰教感兴趣,认为伊斯兰等同于宗教改革中的新教。[12]改革后的伊斯兰教与传统的伊斯兰教相比,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提倡将信仰与尘世生活联系起来,主张每个人与真主的距离是一样的,在生活中的机会也是均等的。[11]129Santri类似于西方的基督教新教,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并这种行为合理化。
《爪哇的宗教》明显体现出格尔茨对于传统民族志整体性的诉求,这个整体性与马林诺夫斯基所强调的整体性有一些差别。首先,格尔茨所负责的对爪哇宗教的调查是项目所预设的爪哇文化的一部分,可见当时的民族志就是建立在参与观察之上的对文化全貌的记录;另外,《爪哇的宗教》本身也在追求一种整体性,格尔茨没有因为偏爱新伊斯兰教而专门加以研究,要讲爪哇的宗教必然包括爪哇的所有宗教即与宗教相关的所有意识和信仰。此外,格尔茨在《爪哇的宗教》中对一些理论的借用也显示这个阶段的人类学者在民族志写作过程中还没有敏感的“自我意识”。譬如,他运用韦伯的相关理论时没有意识到这些理论有可能是以西方为标准而不一定适用于非西方社会。而到了以“写”为特征的阶段,这种意义上的整体性在格尔茨的作品中慢慢淡化而“自我意识”则开始凸现出来。《尼加拉》便是这种转变的极好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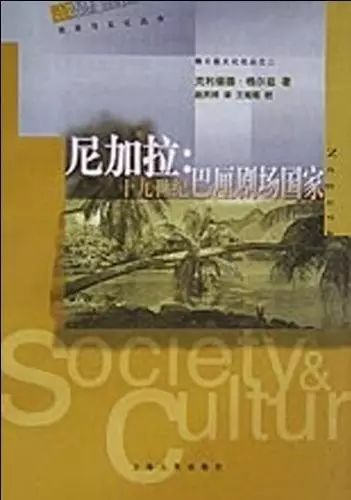
《尼加拉》于1980年付梓,极为明晰地体现了格尔茨有关民族志的主张。格尔茨对于人类学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其中涉及到两个向度,一为本体论(文化是什么),二是认识论(我们如何认识文化);而对于后一点,即对于文化的认识已经从对信息报告人的移情变为对象征符号所依存的公共形式的解释。[13]6与之对应的民族志的写法便从“记”变为了“写”。在《深描: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一文中,格尔茨给出文化的定义后重点是在处理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民族志?格尔茨认为包括民族志在内的人类学者著书本身是“虚构”的产物、“某种制造物”、“某种被捏成形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是假的、不真实的。[5]15这里涉及到格尔茨对于人类学知识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学知识并非来自于社会实在,而是学者式的构造之物。[5]16
格尔茨给出“文化解释”的具体方法:先是展现贯穿于研究对象中的概念性结构(象征符号),接着是针对该结构建立一套分析体系,让这些概念与人类行为的其他决定性因素形成对照,从而呈现符号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5]27格尔茨在《尼加拉》中重述了这一观点。而且在整本民族志的写作中也紧紧遵照着这个方法。
格尔茨先是指出现代政治话语中“国家”(state)这一关键词实际上具有三个层面的意蕴:等级(如级别、地位)、荣耀(如夸示、尊严)以及治理(如体制、控制),但以往的政治理论几乎用“治理”覆盖了“国家”的全部内涵。因此,不论是霍布斯,还是左派马克思主义亦或是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无一不是在实效性的层面上强调政府作为国家合法代理人所实施的权力诈骗术,[14]145-148而忽略了“国家”的象征性层面。从这个“国家”概念出发,政治组织的研究者,诸如马克思、韦伯都采取了一种二元模式:国家与社会;落实到对印度、中国这样的帝国政治的分析中,这种二元模式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与村落共同体。研究的焦点是二者之间的关系:要么乡村组织与地方精英完全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要么村庄形成了与上级政权对立的强大自治组织,或者是在二者间找出一个中间阶层,如中国的乡绅阶层,平衡着二者的关系。
接着,格尔茨从西方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治理)出发对巴厘的政治机体进行平静的描述。他在巴厘也找到了二元对立的两极——尼加拉与德萨,19世纪的巴厘政治形式便诞生于此两极之间。“尼加拉”是巴厘的本土观念,是指“宫殿”、“首都”、“国家”、“领土”以及“城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描述的是由传统城市、其中的超凡政治权威体系以及城市所孕育的高等文化所组成的世界。“德萨”的意思是“乡村”、“地区”、“村庄”、“地方”、“属地”或者是“被统治地区”,在实体上,德萨包括乡村居民、农民、佃户、政治国民、人民。[14]2在空间地理位置上,德萨位于尼加拉的宫殿之外,一个尼加拉对应着一个或多个德萨。
尼加拉建立在三种制度之上:种姓制、亲属制度和庇护关系,德萨的主要组织机构为村庄、灌溉会社和庙会。水稻是巴厘的主要经济作物,灌溉体系在巴厘极为发达,“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因此断言巴厘是水利灌溉型社会,君主通过对灌溉系统的控制而达到政治上的专制。但格尔茨认为巴厘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君主,其次,灌溉会社也并未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中,它拥有自己的地方性组织,处理日常事务并提供道德约束力。所以,格尔茨认为巴厘并非“东方专制主义”,但这也并不是说,作为地方共同体的德萨是自我封闭,完全自治的。在尼加拉与德萨之间,存在着一种Perbelel体系,其成员类似于地方官员,主要负责在村庄中招集农民为王室处理日常生活事务;通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投靠Perbelel。但是,农民与王室的这种关系是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因此,巴厘并没有发展为韦伯所定义的官僚制国家。也就是说,尼加拉既没有统治型的国家机器,也没有基于对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权力机构,正如格尔茨所言,巴厘的国家结构其实是离心的。[14]19那么,尼加拉何以可能?换句话说,使得尼加拉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那个力量来自何处?
由此进入到该书的最精彩部分。格尔茨认为这一力量来自于巴厘的王室庆典,它具有一种向心力,统摄人的心灵,它就是巴厘政治的驱动力。尼加拉犹如一个剧场国家,国王与王公们是主持人、祭司是导演、农民是支持表演的演员、跑龙套的和观众。[14]12没有控制与服从,只有地位、等级差异的展演,“全民”被一场仪式整合起来。这背后隐藏的则是巴厘人关于国家本质的观念,它被称之为“典范中心观”,即王室是神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秩序的物化载体;它成为文明的标准,必须展现为一个典范、完美无瑕的意象。[14]13它也因此成为人们生活所要遵照的一个模式。
全体人民是如何被卷入尼加拉事务中的?这明晰地体现在一个君王的葬礼之中。对这场葬礼的记述出自一位荷兰学者之手,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一场葬礼,更是一场体现巴厘野蛮与未开化的葬礼。借助于他的记录,格尔茨展开对巴厘国家仪式的文本式解释。葬礼本身由一系列象征符号组成:莲花宝座、林加、布蛇、狮形棺椁以及牺牲者头上的白鸽等;这些符号一同构成一个意义体系,即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融合。再次强调了君王的神性、完美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仪式的高潮国王成为君临天下的世俗神。人们对于神以及神的世界的崇拜,转化为对与君主及其尼加拉的膺服。这就是尼加拉的全部内涵:没有控制、命令、力量与服从,国家一样得以可能。
格尔茨对权力的象征机制进行描述并解释这种权力的诗学在巴厘社会中的作用,并与前面所描述的政治机体形成对照,从而得出在巴厘权力诗学比实证主义者们所推崇的权力结构(the mechanics of power)更为重要,它才是巴厘政治的本质。[3]实际上,格尔茨并没有否定祭祀群体、村落组织以及贸易等政治机体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被西方政治学话语一直遗忘的诗学的政治尤其在有非西方社会中甚至更为本质,从而反思此前西方学者冠之以“封建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7]
从写法上看,《爪哇的宗教》与《尼加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背后隐含着格尔茨不仅在方法论更是人类学理论上的发展轨迹。《爪哇的宗教》是对实证主义时代的最后祭拜,而《尼加拉》一方面是解释人类学在民族志上的完美运用,同时向后还开启了一个“写文化”的时代。
三、余 论
“写作固定下来的是什么?……是说话这个事件的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沿着法国哲学家利科的诘问,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原先遵循的呆板标准“观察——记录——分析”已穷途末路;人类学的书写应该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对意义的推测,渗透其中的是人类学者的想象,最终达到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理解。如果说《爪哇的宗教》还严格遵守着“观察——记录——分析”模式,那么,《尼加拉》已然是一个民族志写作时代的典范.
人类学民族志存在一个变化的主线,即对马氏以及布朗所树立的民族志规范的遵守、拓展和反思。[10]在这条主线上,格尔茨应属于拓展性的中间人物,他的贡献就是将民族志从“记”带入到“写”的时代。1967年,马氏的田野日记被公布,在整个学界对马氏愈发陷入道德谴责时,格尔茨指出这项工作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15]72八十年代美国人类学逐渐掀起的关于民族志的文化批评,其成员如保罗·拉比诺是其嫡传弟子,乔治•E•马库斯与詹姆斯•克利福德则是格尔茨亲自邀请至普林斯顿的,正是在这里,马库斯草拟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初稿。人们通常认为格尔茨对人类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给出的关于文化的新定义,在人类学民族志方面,后现代的反思就是基于格尔茨的这个文化概念的而展开的。[13]1但是格尔茨自己却不愿意在后现代的舞台上发出声音。
早在1977年,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相呼应的一本民族志《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付梓,该书作者保罗·拉比诺是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时候的一个博士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实验,拉比诺将田野经历本身作为描述对象。罗伯特·贝拉(Robert N.Ballah)在该书的序中说道:“田野资料不是自在之物,而是我们获得它们的过程的建构之物”。[16]xi布迪厄在该书的跋中认为该本民族志的价值在于“与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条’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17]163。但是作为拉比诺的导师,格尔茨并不是非喜欢和推崇这本民族志,他认为这种反思太过沉溺于沉思与自省以致于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
单就民族志写法而言,《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可以代表两个时代。《尼加拉》迟于《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三年问世,《尼加拉》的写作风格以及思考的议题似乎是在表明格尔茨对后现代主义的谨慎,也说明他更愿意独自寻觅僻静之途。与实验民族志相比,格尔茨走的这条小径同样也是人类学民族志摆脱后现代困境的出路之一。[18]88
注释:
[1]Geertz,Clifford., Works and lives : the Anthropologistas Author[M].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Foucault,Michel.“What is an Author?”[A]//. Josue V. Harari, ed. Textual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C].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3]张桂萍.《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J]//学习与探索.2004(1):118-24.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Geertz,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s : Selected Essays[C].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6]潘英海.文化的诠释者——葛兹[A]//黄应贵主编.见证与诠释:当代人类学家[C].台北:正中书局,1992.
[7]BenedictR. Anderson. Review[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1,(86):1137.
[8]Inglis,Fred., Clifford Geertz:Culture, Custom, and Ethics[M].Cambridge,UK; Malden,MA:Polity Press.2000。
[9]Geertz,Clifford. After the Facts: Two Countries,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10]高丙中.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J]//思想战线.2008,(1):17-22.
[11]Geertz,Clifford.The Religion of Java[M].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12]Hanler,Richard. An Interview with Clifford Geertz[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1, (5):603-613.
[13]Ortner,Sherry B. The Fate of "Culture" : Geertz and Beyond[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4]克利福德•格尔茨著.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M]. 赵丙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克利福德•格尔茨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C],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0.
[16]Ballah,Robert N.“Foreword”.Rabinow’s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in Morocc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17]Bourdieu,Pierre.“Afterword”. Rabinow’s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77.
[18]Marcus,George E. The Use of Complicity in the Changing Mise-en-Scene of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A]//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